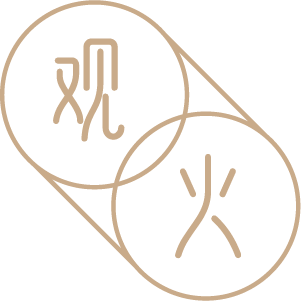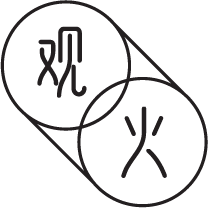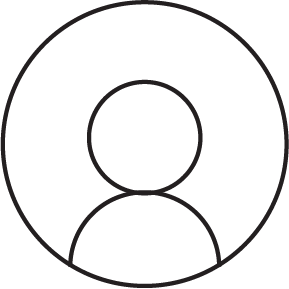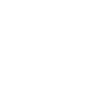2017年2月4日,我在Yak Kharka,给嫂嫂留了言,希望能够和母亲通话,但母亲已回老家,我没办国际连线,母亲的手机又没有互联网服务,只能作罢。我很少在旅行时和家人联络,当时会如此冲动,其实是因为心里有股不祥的预感,好像即将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想听一听老妈的声音,后来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复,就离开了Yak Kharka。
2017年2月5日,继续上路往Thorang Phedi base camp,再到high camp,因为当地没有互联网服务,就再也无法联系上家人了。在人挤人的火炉旁取暖谈天时,往年和家人一起守岁的画面一闪而过,只是短暂的,然后就被屋里的一阵笑声带过。当晚在high camp如预料般失眠,窝在双层棉被里辗转,对家人的思念终于爬墙钻被,直到闹钟响起。
2017年2月6日,凌晨四点半,预计气温零下40度C,high camp的餐厅里坐着登山客们,大约二十来人,经过昨夜在火炉前相互挤着取暖后,算是彼此认识了,那可是肩贴着肩,臀黏着臀所迅速培养出来的关系。大家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此时凑在了一起,只因有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翻过这个海拔5416公尺,世界最高的垭口 – 陀龙垭口(Thorang La)。
吞下最后一口抹上蜜糖的Tibetian bread,满足地用手背擦了一下口,当作了事,确实是有点脏,但在纸巾快用完,水已结冰的前提下,别无选择。我走向大门,做了最后的检查,然后把头灯打开,Sabin拉开了大门,寒意顷刻间充斥了屋内的每一处,我吸了口气,做好即将被冻僵的准备,鼓起勇气,跨出了那扇门。
失去温暖的避风所,有点不舍,我仿佛还能听到从屋内传出来的笑声,还有老板和面团时拍打桌面的声响,只是我已渐行渐远,最后终于失去了那一丝从屋内透出来的微光。此刻的我,在这乌漆嘛黑的雪山上,身上再多的技能全是无用武之地,在陌生的环境里,黑暗让我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
大地超寒,微风刺骨,四周漆黑目不视物,视线就只剩下足前那盏头灯所能照亮的小白圈圈,范围的直径不到一公尺,幸好天边挂着半圆不亮的初十之月,勉强能辨认Sabin和Ishor走在我跟前的身影。脚下是逐渐攀升的崖边小径,内侧积雪覆盖了半个小径,只剩下十二寸左右的宽度是较薄的积雪,勉强能行,我一再提醒自己得加倍小心,因为右边是深不见底的雪坡山崖。
我忘了那一瞬间到底在想些什么让我分了心,也不记得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那是离开high camp大约三十分钟后,我突然脚下一滑,失足跌落右边的雪坡上。
那是个自由滑落,我趴在光秃秃的雪坡上一直往下,双手胡乱挥动着想要捉住些什么却无从着力。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如果停不了这向下之势,那崖底等着我的到底是什么呢?抛开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觉得现在最要紧的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开口喊道:“Help......!”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