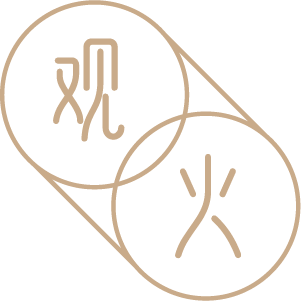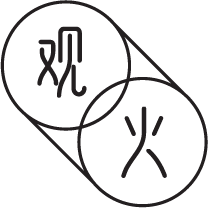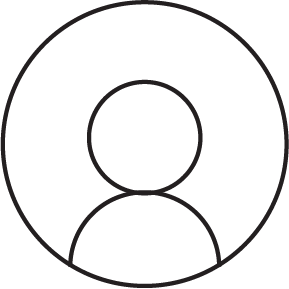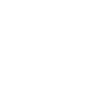话说我们从游轮上下来后,就和一对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情侣一起结伴到阿斯旺的西岸去,我们先到被称为植物园岛的Kitchener’s Island参观,然后才到只有阿斯旺特有的努比亚人村庄里去走走,看看这群古来民族是怎样在历史的变迁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让自己融入现有的社会中。
在motoboat开往努比亚村时,眼前就出现了让人惊叹的景色。当时是难得的风平浪静,所以河水上的倒影显得非常清晰,如此的水中倒影我倒是在印度的Chandra Taal月湖见过一回(印度寻源中湖之心篇里写过),只是两个地方给人的感觉不一样。这里是尼罗河畔,连成一线的是那静淌的河水,沿岸的绿洲和无际的荒漠,努比亚人就在这片河水与黄沙交接之地生存不息,代代延绵,才有了今天的面貌。
努比亚人是生活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区和苏丹北部的当地原住民,他们名字的由来就取自他们的发源地努巴,在公元前6000年,这里已经存在着类似社会组织的形式,和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差不多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努巴的名字就是来自古埃及语中的‘Nub’这个词,意思是黄金,可想而知这里的矿物资源在古时候是多么的丰富。随着古埃及的日渐强盛和统一(约公元前3100年),资源丰富的努巴就成了埃及想剥夺的对象,努比亚与埃及就是伴随着战争和掠夺的方式往来的。虽然相对的弱小,但这两大王国之间的战争彼此有输赢,努比亚还曾经一度的占领了整个埃及。
努比亚人的身体特征具有尼格罗人的一般特点,就是黑皮肤、高颧骨和卷发。虽然现在大多数的努比亚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受到了阿拉伯人的同化,但至今还保留着身体的特征及不少祖先们留下来的文化。他们喜欢斑斓的色彩,房子里外都被粉刷成鲜亮的颜色,不论男女都会在手指和脚趾甲上涂上鲜艳的指甲油,身上也会纹有民族图案,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特色之一。
在motoboat靠岸之前,这是其中一间努比亚人房子的外观。
村子里都是颜色鲜艳的民居,矮矮的北非式房子和那些找不到规律的路道,到处是穿着埃及南部传统长袍在工作的男人,一些屋前的妇人正用掺杂着努比亚口音和阿拉伯语在交谈着,还有在水里嬉戏的小孩子们的笑声,这些灵动的生活瞬间,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面。
正值五月末夏日的正午,我们没有到处走,只在其中一家像是专门招待旅客的努比亚屋里坐着打法时间。这家主人几次过来询问我们是否用餐,我们没有点餐,但想想主人应该是靠客人点餐才能赚钱,这样免费坐着有点不好意思,再加上后来看到了主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发了恻隐之心,就点了几杯饮料当作弥补。其实这件事情上再次证明了我之前对欧美游客的印象,有时他们会比亚洲人还要抠门,因为美国同伴不点餐,我们也不好意思吃,就算在离开之前他连一杯饮料的钱也不让主人赚到,也没主动给点小费,算是一路小气巴拉到底了!
是否还记得之前我在‘沙漠等雨’的‘鬼斧神工,阿布辛贝’篇中曾提过,联合国的工作者们联合了51个国家的力量,用资高达美金40亿的情况下把整个阿布辛贝神庙搬迁吗?你觉得在建起阿斯旺高坝、形成纳赛尔湖的时候只有神庙古迹被淹没湖底吗?其实从二十世纪初,从埃及政府决定建造阿斯旺水库起,沿河的努比亚人就注定了多次迁移的命运。最大的一次搬迁是在阿斯旺高坝建造时期,这是第四次的水位攀升,共1万8千个家庭的屋子被淹没。
在这片旧时的黄金之地,或许地下的宝藏已被掏空,或许原来的避风之所已淹没湖底,但努比亚人还是一直梦想着回到昔日生活的村庄,如今的纳赛尔湖畔。他们因为埃及政府宣布努比亚人将优先获得位于古努巴地区的土地而感到庆幸,在政府实施的纳赛尔湖地区重建和一些大型土地开垦项目中,努比亚人再次看到了回归的希望。
预告:
2019年的夏天,从阿斯旺回来以后隔天就走在了回家的路上,结束了这一趟最炎热的旅程。本以为会在隔年再游一趟埃及,谁曾想同年的冬天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全世界进入封闭模式,一关就是两年。今年新年期间再游一趟埃及,旅游时的心境在疫情下明显已不同,而今年的埃及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