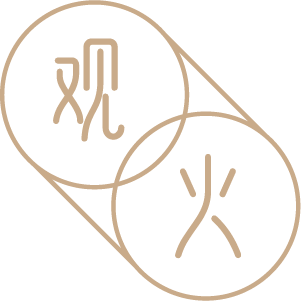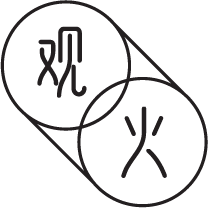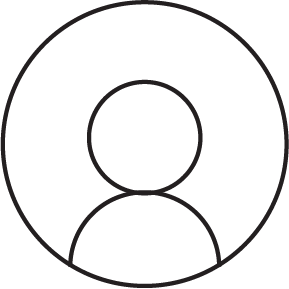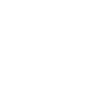看电影是我的嗜好,看完撰文是我的本能,都随着岁月成长而不断演变。回顾来时路,当年观影的一些印象依稀,但感受还是很实在地烙印在心底,关于我的口味和情绪滥觞,就让这一篇娓娓道来。
儿时依稀的银幕初体验
1970年出生的我,已经不可能记得第一部在戏院看的是什么电影,存留在我脑海中最早的银幕记忆是许冠文和许冠杰在路边的对话,其中一句是:「那个傻佬不就是我咯!」后来在电视上重看这部电影,才晓得那是《鬼马双星》,许氏兄弟的银幕首炮,翻查资料发现是1974年的电影,当年破了香港票房纪录,我父亲从此成了许氏电影的影迷,每一回都带我们一家人进戏院捧场,随后的《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无一错过。我童年的电影印象还包括台湾文艺爱情片,林青霞林凤娇秦汉秦祥林成双成对,还有年轻的刘文正配搭张艾嘉,唱了一大堆电影歌曲,当时有看没有懂,只记得大家裤脚很阔头发很长。西片主要是Roger Moore主演的007电影,以及印象深刻的大地震、大白鲨、金刚和火烧摩天楼,演员是谁不重要,只要看大场面就满足了。
电检尺度新不如旧
我儿时住在槟城乔治市牛干冬(Chulia Street)大街,方圆一里之内可以步行抵达的戏院有15间之多,看电影非常方便。不过我童年时代一直是跟着家人进戏院,看父母选看的影片,一直到了13岁升上中学后才开始自己购票看电影。那时候的银幕尺寸相对开放,露点的画面经常出现,也没有打格子处理,报章广告还会用大胆香艳的字眼宣传,标榜成人电影。这些广告一直让我感到好奇,所以第一次自主买票看的就是这一类片种,记得当时是搭巴士到柑仔园路的星光戏院观赏一部由台湾艳星陈丽云主演的社会写实片,片名已经忘了,只记得当时这类电影以拳头和枕头挂帅,借社会写实为名,大卖暴力与色情,被后世称为“台湾黑电影”,从1979年盛行到1983年,催生了陆小芬,杨惠姗、陆一婵、陆仪凤等作风大胆的女星。那时候的戏院经常会拿一些过时的日本风月片和西方情色电影播放,大部份都删剩寥寥无几的情欲镜头,但青春期的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相比如今趋向保守的电检尺度,当年的银幕精彩多了。那时港产片还没有实施分级制,像《靓妹仔》和《烈火青春》的题材和意识就比后来的三级片还要大胆。
观影管道不断演变
由于父母不喜欢科幻题材,我上了中学才开始看星战电影,那时已经是早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Star Wars: Return of the Jedi》,我连《E.T.》都是后来看电视台重播的。说到电视台,虽然当年只有国营的RTM1、RTM2和私营的TV3,但我也从中观赏到不少经典电影,如《Citizen Kane》、《Psycho》、《It's a Wonderful World》、《儿子的大玩偶》、《半边人》等等中西名片,是戏院以外另一个提供我电影养份的管道,有一些还被我用录影带录起来重复观赏。录像带出租店的盛行也成了我寻宝之地,在一大堆香港连续剧的围绕下,偶尔找到一两盒《The Shining》和《Blade Runner》这类想看的影片,那份喜悦非笔墨所能形容。毕业后迎来翻版影碟的盛世,不少国内看不到的电影所引起的遗憾都可以从中得到弥补,各类大师级作品和禁片都在搜集名单上,选择比院线多了几十倍,这就是现实。来到21世纪的网络世界,资源之丰富让我可以完全自主,从分享档案到串流平台,只怕你没有时间看而已。如今的我上戏院是一种习惯,上网则是一种需要。
大型旧戏院的记忆
以前大型旧戏院时代,我通常都是买票价一元的楼下二号位,那是中间位置,不靠前也不靠后。那时的戏票还是人手划位,可惜我没有收藏起来。遇到卖座电影上映,戏票一早被黄牛党买完,小时候一家人为了不想扫兴而归,父亲只好忍痛高价买下,我后来自主买票后,就从来没有光顾过,有钱都不给这些人赚,好几次宁愿坐到第一排全程仰望银幕都在所不惜。以前的戏院一天四、五场都是播放同一部电影,但奇怪的是总是有人进场,我还没试过一个人包场,最冷清的一次是在车水路丽士戏院观看U2的音乐纪录片《Rattle and Hum》,那个下午全场除了几个马来青年外,就只有我和我的同学。80年代也有不少明星随片登台,我唯一一次的追星是在《开心鬼放暑假》的下午场,在槟榔律奥迪安戏院的停车场争睹开心少女组的三位成员上车,我追看的是年纪最小的袁洁莹,她只比我年长一岁。看电影是当时中学生每回考试最后一天结束后的庆祝方式,去到任何一间戏院都可以看到来不及换下校服的年轻人。
观影口味的转捩点
和大部份观众一样,我一开始也是追求感官刺激,越煽情的情节越受落,小时候看《八百壮士》看到死那么多人去升一面国旗觉得很感动,看民间故事梁天来冤案的屡告屡败会看到想哭。我看电影的口味转折出现在中学时代,那时在华文学会翻阅了几本过期的《学报》,被里面谈电影的文章和观后感给吸引住了,这才发现看电影有这样多的学问和角度,不只是娱乐那么简单。其实这本刊物早在1983年停刊,我是在翌年才接触,可说是迟来的启蒙,让我开始认真对待观影这回事,对电影有所要求。过后又在同一个学会认识了爱看电影的学长陈文贵,跟着他到法国文化学会观赏经典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虽然当时一窍不通,只能囫囵吞枣,但也因此初开眼界,知道天外有天,当年消化不来的内容,却在往后的日子不断反刍,成为一种观影的视野,影响深远。当我对观影有了自己的要求和审美观以后,就开始发展到文字书写,在尝试推介音乐与戏剧之余。电影成了下一个目标。我把第一篇观后感投稿给槟城光明日报副刊的《电影定格》,被编辑卓昌敏和欧宗敏采用,刊登在1992年10月11日星期天的版位内,当时写的是一部在法国文化学会播映的法国片《非洲的女人》(La femme en Afrique),初试啼声写得像一篇散文,纯碎是有感而发。有关版位早已不复存在,但写作却一直持续至今,辗转28年,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